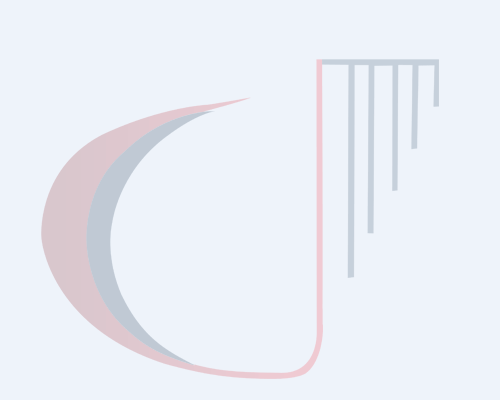白蟻防治服務的定位分析
白蟻是一種古老的社會性昆蟲,白蟻危害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我國的白蟻防治服務開展已進行了幾十年,長期以來基本上是按照國家的有關(guān)政策規(guī)章,在行政主管部門的管理下,由政府下屬的白蟻防治機構(gòu)負責所屬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白蟻防治服務。行業(yè)服務目的集中體現(xiàn)其積極的社會效應、單位良好的行政服務和公益形象。但隨著近年來我國市場經(jīng)濟體制建設的日趨完善與成熟,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白蟻防治體制就面臨著如何解決與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不相適應的一些問題,如政事企不分、機制不夠活、功能單一等,白蟻防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另外社會資本希望介入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呼聲日趨強烈。目前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方向及管理理念面臨著重大的轉(zhuǎn)變,因此對我國白蟻防治服務的科學定位就顯得十分重要。希望通過運用公共經(jīng)濟學的公共產(chǎn)品理論對白蟻防治服務進行分析,從理論上來合理界定我國的白蟻防治服務,為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管理提供理論依據(jù)。
一、公共產(chǎn)品理論概述
1、社會產(chǎn)品的分類及依據(jù)
社會所提供的可供人們消費、滿足人們各種欲望的物品和服務(即社會產(chǎn)品),按其在消費過程中的消費特征的不同,可以分為公共產(chǎn)品(public goods)、私人產(chǎn)品(private goods)和準公共產(chǎn)品(quasi-public)三大類。
消費過程的消費特征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描述,即消費的競爭性和消費的排他性。消費的競爭性是指某人對某一社會產(chǎn)品的占有和消費,會使他人無法占有和消費,除非增加這一社會產(chǎn)品的供應,更嚴格地說,就是消費的增加會引起邊際成本的增加。與之相對的是消費的非競爭性,在非競爭性的條件下,某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不會引起他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即對非競爭性物品消費的增加不會要求供給的增加,也不會引起邊際成本的增加;消費的排他性是指社會產(chǎn)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利益能為某些人或某個人所專有,也就是說人們可以通過經(jīng)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或技術(shù)的辦法將某些消費者合理地排除在對某項產(chǎn)品的消費之外。與之相對是消費的非排他性,即不可能有效地將某個人或某些人排除在該物品的受益之外,或者是技術(shù)上的不可能或者是經(jīng)濟上的不可能。
2、公共產(chǎn)品與私人產(chǎn)品
自蘭度爾首次提出公共產(chǎn)品的概念以后,目前已在公共經(jīng)濟學領(lǐng)域得到了廣泛的使用。有不少經(jīng)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定義,如薩繆爾森認為,所謂公共產(chǎn)品就是所有成員集體享用的集體消費品,社會全體成員可以同時享用該產(chǎn)品,而每個人對該產(chǎn)品的消費都不會減少其它社會成員對該產(chǎn)品的消費。或者說“公共產(chǎn)品是這樣一些產(chǎn)品,無論每個人是否愿意,它們帶來的好處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個社區(qū)里”;奧爾森認為“任何物品,如果一個集團中的任何個人能夠消費它,它就不能適當?shù)嘏懦馄渌藢υ摦a(chǎn)品的消費”,則該產(chǎn)品是公共產(chǎn)品。換句話說,該集團或社會是不能將那些沒有付費的人排除在公共產(chǎn)品的消費之外的,而在非公共產(chǎn)品那里,這種排斥是可能做到的;我國的經(jīng)濟學家梁小民、睢國余、劉偉等認為“某一種公共產(chǎn)品只可以使很小的團體,比如包括兩個人的小團體收益,而另外一些公共產(chǎn)品卻可以使很大的團體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受益。”
雖然對公共產(chǎn)品概念有不同的定義,但對公共產(chǎn)品的消費特征大家較為公認,公共產(chǎn)品在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兩大特征:第一消費的非競爭性。公共產(chǎn)品的非競爭性意味著增加消費者引起的社會邊際成本為零,在公共產(chǎn)品的消費上,人人都可獲得相同的利益,而且互不干擾。例如,一個國家的國防系統(tǒng)使該國的每一居民都可享受同樣的好處;第二消費的非排他性。公共產(chǎn)品一旦提供就不能阻止另外一些人從中受益,或者是因為技術(shù)上的不可能,或者是因為排除成本的高昂而無法把受益范圍內(nèi)某人排斥掉。因此公共品在其受益范圍內(nèi)具有共同消費的特點,即使有技術(shù)上的可能性,但由于排除費用過于高昂,以至得不償失不得不放棄。
公共產(chǎn)品之所以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是因為公共產(chǎn)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某人對某公共產(chǎn)品的消費,便等于對其全部的消費,生產(chǎn)提供的數(shù)量等于每個人消費的數(shù)量,而且每個人也消費同樣的數(shù)量。公共產(chǎn)品消費的非排斥性意味著,它一旦生產(chǎn)出來,就如普照之光惠及全體社會成員,而不論每個社會成員是否支付了費用。這正如大衛(wèi)·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公共產(chǎn)品一旦被生產(chǎn)出來生產(chǎn)者就無法決定誰來得到它,這就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可以“免費搭車”。
私人產(chǎn)品是供個人消費或使用的物品,它具有與公共產(chǎn)品完全不同的消費特征:第一消費的競爭性。某人對私人產(chǎn)品的占有和消費會使他人無法占有和消費,除非增加成本生產(chǎn)出更多的私人產(chǎn)品;第二消費的排他性。人們可通過技術(shù)上可行、經(jīng)濟上合理的手段將某些消費者排除于對某項私人品的消費之外。與公共產(chǎn)品相比私人產(chǎn)品具有可分割性,私人產(chǎn)品在消費者之間是完全可分的,消費的對象是可以區(qū)隔的,消費的數(shù)量是可以累加的。
3、準公共產(chǎn)品
從傳統(tǒng)理論上講,準公共產(chǎn)品是介于公共產(chǎn)品與私人產(chǎn)品之間的社會產(chǎn)品,它是具有公共產(chǎn)品與私人產(chǎn)品特征的混合產(chǎn)品。對它的消費特征的描述有三種不同表述:
(1)準公共產(chǎn)品是具有外部性的私人產(chǎn)品。羅森認為純粹的私人產(chǎn)品除了具有消費的竟爭性和排他性外,還具有消費的獨立性,即沒有外部的或者溢出的影響,而當物品滿足前兩條件但不滿足第三條件時,就是準公共產(chǎn)品。
(2)準公共產(chǎn)品是具有消費的竟爭性但無排他性,或者具有消費的排他性但無竟爭性的物品。準公共品有兩類:一類是具有消費的竟爭性但無排他性的物品,如垃圾處理及孤兒院、養(yǎng)老院等社會福利服務;另一類是具有消費的排他性但無竟爭性的物品,如公共衛(wèi)生、教育、社會保險等。日本經(jīng)濟學家植草益認為,第一類準公共產(chǎn)品不具有排他性,因而價格形成困難,只能采取免費供給方式;而第二類由于具有排他性,因而有可能向主要受益者收費,它可以與私人品一起合稱為“市場性物品”。
(3)準公共產(chǎn)品是“俱樂部物品’(club goods)。美國經(jīng)濟學家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認為:“有趣的是這樣的物品和服務,它的消費包含了某些‘公共性’,在那里適度的分享團體多于一個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個無限的數(shù)目。‘公共’的范圍是有限的”。這種介于私人產(chǎn)品和公共產(chǎn)品之間的“俱樂部物品”既有別于私人品,又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品,其消費特征表現(xiàn)為:第一局部的排他性。俱樂部物品對其成員來說是非排他的,但對非成員來說是排他的;第二有限的非竟爭性。在一定的消費容量下,單個會員對俱樂部物品的消費不會影響或減少其他會員對同一物品的消費,而一旦超過臨界點,過多的會員加入非竟爭性就會消失,擁擠就會出現(xiàn)。
二、白蟻防治服務的內(nèi)含、特點及發(fā)展
1、白蟻防治服務的內(nèi)含及特點
所謂白蟻防治是指人類采取一定的措施阻止白蟻接近、取食木材及其他人類需要的纖維材料,消除因白蟻活動而造成對人類生命財產(chǎn)安全損失的活動。白蟻防治服務作為一種社會產(chǎn)品,主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服務對象的廣泛性。白蟻是破壞性極大的世界性害蟲,白蟻危害涉及房屋建筑、水庫堤壩、農(nóng)林作物、通訊設備、交通設施、園林綠化等多個領(lǐng)域。據(jù)估計,我國房屋建筑每年因白蟻危害造成的直接經(jīng)濟損失約20~25億元。白蟻對文物古跡、水庫堤壩等造成的間接損失則更為巨大。由于白蟻危害大并已關(guān)系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白蟻防治服務對象廣泛,涉及國民經(jīng)濟的許多方面。
(2)服務資源的稀缺性。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全國約有白蟻防治專業(yè)機構(gòu)1000余家,其中事業(yè)性質(zhì)單位約600家,企業(yè)性質(zhì)單位約400家。全國白蟻防治行業(yè)從業(yè)人員約11570余人。相對于白蟻防治服務的巨大需求,其服務資源的稀缺性是十分明顯的。
(3)實施的復雜性。白蟻防治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代表直接服務對象的利益,同時也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但由于存在白蟻危害嚴重性、白蟻服務質(zhì)量、白蟻服務成本等的信息不對稱性,白蟻防治服務的實施涉及政府、服務機構(gòu)、服務對象等多個層面。一些事務需要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xiàn),一些事務是服務單位與對象難以實施或不愿意承擔的。
2. 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形成與發(fā)展
目前,我國白蟻防治服務的主要對象有兩部分:一是水庫堤壩、林木的白蟻防治;二是房屋建筑的白蟻防治,其中房屋建筑的白蟻防治要占到絕大部分。房屋建筑的白蟻防治包括新建房屋的白蟻預防和原有房屋的白蟻治理。
我國的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形成與發(fā)展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十世紀50年代到80 年代中期,以白蟻滅治為主的時期。這個時期主要開展群眾性滅治白蟻運動,一些蟻害地區(qū)的大中城市建立了白蟻防治的專業(yè)機構(gòu),白蟻預防是在建設單位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二階段是從1986 年至1999 年,“以防為主,綜合防治”時期。1986 年,浙江省率先爭取到了有關(guān)部門領(lǐng)導的同意并發(fā)文,在浙江省范圍內(nèi)開展了新建房屋建筑的白蟻預防工作,1987 年和1993 年建設部分別二次發(fā)文,要求我國各蟻害地區(qū)的新建、翻建、擴建的房屋必須進行白蟻預防。這個時期很多市縣先后都建立了白蟻防治所(站、中心) ,白蟻預防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但全面開展的阻力依然很大;第三階段是從1999 年以后“ 以防為主,防治結(jié)合,綜合治理”的階段。1999 年10 月15 日建設部第72 號令《城市房屋白蟻防治管理規(guī)定》的頒布,是我國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一個重大轉(zhuǎn)折點,我國的白蟻防治服務業(yè)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有蟻害地區(qū)基本上開展了房屋建筑的白蟻預防服務。
近年隨著我國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不斷發(fā)展,白蟻的綜合治理已開始進入實施起步階段。害蟲綜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簡稱為IPM)是指對害蟲進行科學管理的體系,它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總體出發(fā),根據(jù)害蟲和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充分發(fā)揮自然因素的控制作用,因地制宜地協(xié)調(diào)應用一種或多種必要措施,將害蟲控制在經(jīng)濟損害允許水平以下,以期獲得最佳的經(jīng)濟、社會和生態(tài)效益。白蟻的綜合治理是指運用IPM理念進行白蟻防治服務,其特點是以一定的區(qū)域為服務對象。
三、白蟻防治服務的屬性分析
1.消費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
對于白蟻防治服務的非競爭性可從二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由于目前蟻害地區(qū)的各市、縣(區(qū))基本上成立了專門的白蟻防治機構(gòu),負責本地區(qū)域范圍內(nèi)的白蟻防治服務,只要在服務能力的承受范圍內(nèi),任何人對白蟻防治服務的消費不會影響或減少其他人的消費,也不會引起邊際成本的增加。但一旦超過了服務能力的承受范圍,擁擠就會出現(xiàn);另一方面,由于白蟻生存的需要,每一白蟻群體均有一定的活動范圍,即白蟻危害具有一定的區(qū)域性,在同一白蟻群體的危害區(qū)域內(nèi)不存在消費的競爭性。因此白蟻防治服務的消費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
2.受益在技術(shù)上具有的排他性
白蟻防治服務總是針對一定的直接服務對象進行的,具有直接受益的對象。從技術(shù)角度看,白蟻防治服務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可以按照誰付款誰消費的原則,將不付款的人排除在外。當然,由于存在白蟻危害的區(qū)域性,在同一白蟻群體的危害區(qū)域內(nèi)存在一定的非排他性,這在開展白蟻的綜合治理以后會更加明顯。
3.白蟻防治服務存在外部性
白蟻防治服務的外部性主要表現(xiàn)在二個方面:
(1)消費的外部性。白蟻活動具有較大的活動范圍及較強的擴散遷移能力,如有的白蟻種類的一個成熟群體,其活動范圍有時達幾千平方米,也就是說一個白蟻群體的危害面積可達幾千平方米,在該范圍內(nèi)有人消費了白蟻防治服務,其它人也就可免費享受;如目前世界上危害嚴重的臺灣乳白蟻,原只存在于我國臺灣等少數(shù)幾個地區(qū),但隨著二次大戰(zhàn)物資的運輸,臺灣乳白蟻的分布范圍擴大,目前已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產(chǎn)生危害,成為世界上危害房屋建筑最嚴重的害蟲,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全世界每用于該種白蟻防治費用超過十億美元。這說明一個地區(qū)的白蟻防治服務將會影響其它地區(qū)的白蟻分布,由此可見白蟻防治服務的消費其效應存在“溢出”現(xiàn)象,其正外部性明顯。
(2)生產(chǎn)的外部性。在進行白蟻防治過程中,必然要采用一定的工藝、方法、藥物進行處理,不同工藝、方法、藥物不僅影響白蟻防治的質(zhì)量,而且也會造成對環(huán)境不同程度的影響。如作為前幾年世界范圍內(nèi)的主要白蟻防治藥物--氯丹和滅蟻靈,它們對白蟻防治的效果十分明顯,對推動白蟻防治工作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由于它們屬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簡稱POPs),在環(huán)境中不易降解,存留時間較長,局部排放的POPs可以通過大氣、水和食物鏈的輸送而影響到區(qū)域和全球環(huán)境。因此POPs已成了由人類活動排放到環(huán)境中最危險的污染物質(zhì)之一,POPs污染問題已經(jīng)成了全球關(guān)注的焦點。經(jīng)過3年多時間的多次政府間談判,2001年5月23日,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90多個國家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簽署了旨在控制和消除POPs污染影響的《POPs公約》(又稱《關(guān)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該公約的簽署全面開始了削減和淘汰POPs的國際合作,2004年5月17日公約對全球正式生效,2004年6月25日我國人大常委會核準公約,2004年11月11日公約對中國正式生效。雖然目前在世界范圍內(nèi)已經(jīng)全面開始了對POPs的控制和污染影響的消除,但需要巨大的社會成本。通過對該事例的分析,可以認為在白蟻防治服務的提供過程中,有可能產(chǎn)生較大的負外部性。
根據(jù)以上分析,可以認為白蟻防治服務是既有公共產(chǎn)品特性又有私人產(chǎn)品特性的準公共產(chǎn)品,而且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和外部性,因而可以通過收費來調(diào)節(jié)供需的平衡,解決擁擠性問題;通過政府的規(guī)制,解決外部性問題。
當然,本文僅僅是通過對白蟻防治服務的屬性分析,從理論上將我國的白蟻防治服務定位為準公共產(chǎn)品,來說明白蟻防治應屬于公共服務的范疇,需要政府、服務機構(gòu)、服務對象等多個層面的有機結(jié)合,才能確保我國白蟻防治服務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至于白蟻防治服務供給方式的選擇、合理定價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